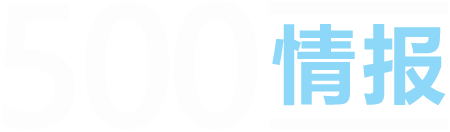彼得·蒂尔的逆反策略
《纽约客》杂志(The New Yorker)在2011年向蒂尔问及此事,他说自己后悔这么写。他对《纽约客》说:“我对与身份有关的问题的思考远比他人更加细致。我考虑基友的感受,考虑黑人的感受,还会考虑女性的感受,这些感受存在着重大的差异。我认为,目前有一种夸大这种感受并且将它上纲上线的趋势。”
在我们的交谈中,蒂尔说在写那本书时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。“现在回想起来,我那会儿应该知道的。只是当时非常困惑,难以置信。”他说。现在,蒂尔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稳定男友,但是他不愿透露更多的细节。(纠结的往事已经形成了闭环,那位高唱反基论调的前法学院学生最近也承认了在与同性谈恋爱。他怎样看待1992年的那件事情呢?他对我说:“我可不往回看,那都是22年前的事情了。”)
蒂尔将他从贝宝赚到的钱中的1,000万美元投在对冲基金上,改名为Clarium Capital,再次开业。他说:“我们在Clarium发展出来的宏观经济大思维便是石油峰值理论。基本内容是全球的石油将消耗殆尽,对此我们并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,没有更多的石油,找不到更多的储量,也没有替代能源。”这也就是他的技术停滞论的第一次闪光。
在风险投资方面,他开始与霍夫曼一起搞天使投资。他俩投资社交网络新创企业,从2003年投资霍夫曼自己的领英开始,到2004年持股Facebook时达到巅峰。
同样是在2004年,蒂尔创立了一家新的新创企业—它的商业模式看上去太不靠谱,一开始没有吸引到任何的硅谷投资。除了蒂尔,它在初期唯一的创投人是一家叫做In-Q-Tel的非营利机构,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(U.S.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)的风险投资部门。
蒂尔解释说:“基本上,我认为贝宝用来打击欺诈的一些办法—欺诈一度对贝宝构成了重大威胁—都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,比如打击恐怖主义。”他说,在“9·11”事件之后,“你看到类似于副总统切尼(Cheney)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(ACLU)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:我们要多些安全少些隐私,还是要少些安全多些隐私?而我担心的是,只要发生恐怖袭击,ACLU一定是输掉的那一方。”
蒂尔认为,这场辩论有被忽略的地方:谁都没有意识到,随着技术的进步,“我们可以在较少侵犯隐私的情况下加强安全。”
为此,蒂尔创办了Palantir公司,为政府情报机构提供数据挖掘服务(是的,很多人觉得一位自由主义者从事这样的项目,是令人吃惊的事)。他强调,这些服务能最大限度地做到不介入和可追溯。10年后,这个市场已经被证明比许多人预测的大得多,去年超过60%的营业收入来自于私营部门客户。经过最近一轮融资,Palantir的估值达到90亿美元。2005年,蒂尔创办了自己的风投机构Founders Fund。2006年,他又创立了蒂尔基金会,通过该基金会资助探索型的慈善项目。目前,基金会每年捐出1,300万美元到1,500万美元。
基金会的早期受益者是奥布里·德·格雷(Aubrey de Grey),他是极具争议的生物遗传学家、人工可忽略衰老策略组织研究基金会(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Research Foundation)的创始人。德·格雷正致力于开发一种能够延缓(或许可以无限期延缓)衰老的再生疗法。在一封电子邮件中,德·格雷向我确认,他依然相信,第一位能活到1,000岁的人现在已经在世了。
蒂尔对抗衰老研究的支持,也许是他作为一名“明确的乐观主义者”最极端的体现。按照蒂尔在《从0到1》书中的定义:明确的乐观主义者相信“如果他计划并努力工作,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,那么未来就会比现在更好”。蒂尔将这种人与“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”进行对照,后者认为“未来会变好,但……他不确切地知道会如何变好,因此他不做任何的具体计划。”蒂尔痛恨后者的态度,他觉得这类人在美国是主流。
蒂尔的第二个“声名狼藉”的慈善项目是海上家园研究所(Seasteading Institute)。2008年,他与别人联合创立了该研究所,旨在当前各国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外建立一座漂浮城市。然而,在我们的谈话中,蒂尔提到这个项目用的是过去时,他强调:“这件事做起来非常难,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文化上。”
而蒂尔最“臭名昭著”的慈善项目大概也就是他的“20位20岁以下企业家”了。该项目为18岁到20岁之间的天才学生提供10万美元,让他们创办自己的新创企业。这个项目赋予“明确的乐观主义者”权力,但是同时彰显了蒂尔的观点:即我们正处于一个“教育泡沫”中,学校欺骗学生,使他们高估学位的实际价值,让他们背上不必要的债务。
该项目遭到了反对。TechCrunch称,前哈佛大学校长拉里·萨默斯(Larry Summers)说它是“这十年中导向最错误的慈善事业”。Slate集团(Slate Group)的董事长雅克布·韦斯伯格(Jacob Weisberg)在《新闻周刊》(Newsweek)上写道:“蒂尔资助的学生们将有机会效法他们的资助者,在成年伊始即停止学习知识,一门心思放在尽可能快地发财上,以此回避帮助他人或单纯追求知识的可怕诱惑。”虽然存在这些争议,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小项目。安德森说:“蒂尔就是这样的人。学校里的人都吓坏了,好像听到了系统性教育的丧钟似的。一年才20个孩子,等一年有2万个孩子的时候再来找我谈吧。”
由于蒂尔作为一位公知的信誉部分建立在其财务成就带来的假定上,2008年金融危机威胁到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,不过他还是挺过来了。
他的对冲基金受到了沉重打击。Clarium原来一直很好地践行蒂尔的石油峰值理论,油价从2002年的40美元一桶一路攀升,到2008年年中,达到近140美元。在这段时间,基金随着所持股票的价格暴涨,基金的规模由1,000万美元膨胀到60亿美元,新投资者蜂拥来找他。
但是到了2009年2月,油价一度回落到几乎40美元。尽管蒂尔已经预见到了房地产泡沫,可还是低估了它。他承认:“我们没有完全相信依据我们的理论对形势的糟糕程度所做的预测。”
更糟的是,他反应过度,错过了反弹,从而导致Clarium在2009年和2010年严重跑输大盘。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出逃。如今,Clarium管理的资金大约是2亿美元,只来自于蒂尔和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几位铁杆投资者。相比之下,他的旗舰风投机构Founders Fund发展得顺风顺水。它管理的资金已经由其第一只基金在2005年封闭时的5,000万美元增长到了其第五只基金在今年3月封闭后至现在的20亿美元。据一位自2007年以来一直参与Founders Fund的资金管理的有限合伙人称,在所有同年期的风投基金(以基金封闭的那一年算)里,Founders Fund的业绩“可以排在前25%,甚至可能排在前10%。”年收益率在35%到45%之间。
蒂尔说,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他的事业,但是这也让人们更加接受他的“科技停滞论”。不过,他的假说只是多了几位接受者而已。曾经与蒂尔在牛津辩论过这个问题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思·罗格夫(Kenneth Rogoff)写道:“现在,大多数顶尖大学的科学家同事对他们在纳米技术、神经科学、能源等前沿领域的项目特别兴奋。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。”
乍一看,蒂尔这本《从0到1》是在规劝企业家们从事变革性的创造,这与他“科技停滞理论”的悲观看法似乎是相违背的。然而,前者正是后者在背后推动的结果。蒂尔向我解释说,当人们谈及未来时,会一致认为全球化继续深化,发展中国家将会变得像发达国家。然而人们没有关注的是,眼下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技术突破正在形成,全球化会带来马尔萨斯式的黑暗现实。他评论说:“如果中国每人都有一辆高耗油汽车,油价就会是每加仑10美元,并且还会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。”但这只是开始,因为没有增长,政局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不稳定终将导致全球冲突,冲突反过来会导致他在2007年的一篇杂文里所提到的“世纪灾难”—人类的彻底灭绝,原因或者是热核战争、生物污染、不受遏制的气候变化,或者是一连串竞相发威的末世劫难。
他带着特有的淡定与轻描淡写的口气说:“所以,我觉得,重要的问题不只是‘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产品?’”(财富中文网)
译者:天逸